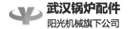2017年3月23日至26日,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今年论坛主题是“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出席并发言。
会后,林毅夫在回答网易财经提问时表示,中国还处于城镇化过程中,房地产依然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性行业,过程中财富向房地产转移是中国城镇化的必然过程。“但是要避免房地产变成投机的手段,就像习主席说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论坛上林毅夫谈到了对中美在未来经济合作方面的看法。林毅夫认为,特朗普对中国很多贸易、经济等等站在“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富强起来”的观点下,认为它的很多问题是中国引起的,但是中美之间其实主要是互补。
“特朗普在选举的时候讲了很多选举的承诺,这种状况之下,中美之间就会有一些紧张的关系。 中美之间其实合作是双赢,这是唯一的选择,但是应该找到一个容易谈的地方开始来谈,大家有共识的地方,比如说用基础设施作为经济下滑的时候的一种财政政策,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经验。”林毅夫说。
以下为发言实录:
媒体:您大概1月份的时候在美国纽约建议特朗普采用中国的增长方式,4月特朗普和习近平可能会见,您觉得他们会不会就相关方面达成一些什么共识?5月份“一带一路”论坛又要召开了,您对中美未来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有什么看法?
林毅夫:中美关系现在是国际上非常关注的,因为美国是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的经济体,老大跟老二之间要是关系紧张的话,影响的不仅是老大、老二。
特朗普对中国很多贸易、经济等等站在“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富强起来”的观点下,认为它的很多问题是中国引起的。我刚刚参加另外一个论坛,大家理性地分析,认为中美之间其实主要是互补,两方的合作是共赢的。当然,总体上来讲是很清楚的,但是特朗普在选举的时候讲了很多选举的承诺,这种状况之下,中美之间就会有一些紧张的关系。
但是中美之间其实合作是双赢,这是唯一的选择,但是应该找到一个容易谈的地方开始来谈,大家有共识的地方,比如说用基础设施作为经济下滑的时候的一种财政政策,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经验。而且这个成功的经验,像我是在世界银行2009年的时候开始推行这个概念,当时同意的人比较少,并不是他不同意我的分析,是因为当时大家认为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可能跟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发生的金融经济危机一样,三个季度到七个季度,这种状况之下只要发失业救济、维持社会稳定就好了。
但是当时我判断它可能是长期危机,长期危机你单单发失业救济是不行的,因为你单单发失业救济的话,政府的开支增加,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的财政减少,赤字会增加,这长期是不可持续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找到一个什么办法,找了一个办法短期能创造就业,减少失业救济的需要,长期还能提高生产率,发失业救济不能提高生产率,吃了就没有了。但是对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在短期创造就业、减少失业救济的需要,长期消除增长瓶颈,生产率水平提高,财政收入增加。并且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建基础设施的成本也最低,因为各种材料价格低。
我很高兴现在国际上逐渐变成共识,比如说2014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它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当中也在强调,经济下滑的时候是基础设施投资最好的时候。在20国集团从2010年首尔峰会开始也强调基础设施,我们去年杭州的峰会也强调全球基础设施,那就是在国际上有共识了。特朗普现在也强调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所以他准备在美国推行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既然这些大家有共识,就容易谈。
就像中美之间在奥巴马的时候,当然,中美之间也有不少争议,但是在全球气候变暖上是有共识的,所以中美合作2015年就达成了《巴黎协议》。我也希望这一次我们习主席跟特朗普见面的时候,从大家有共识的地方作为双方讨论的切入点。当然,达到共识以后,当双方能够牵手认为你对、我对、对我好对我好对世界也好,在这个基础上气氛就不会那么僵,可以再谈其他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只要能坐下来谈,不管是从理论的分析和实战的经验,我都认为中美之间其实在经济上是互补的,美国如果说实行保护主义,中国有一句话,“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
媒体:实体经济大家都说不好做,制造业更难,这都是工业问题比较突出,我想问一下党和国家目前需要怎么样的工业精神,这种精神怎么样才能建立起来?
林毅夫:我想有两点,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的国家,肯定有不少体制机制问题,容易面对,容易改革。另外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当前的经济困难,除了我们自身有待完善的地方之外,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周期的问题。
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滑,从10.6下滑到去年6.7,去年是从1990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慢的年份。从2010年到现在持续七年的时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曾有过的,这是事实。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世界上跟我们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情形也一样,而且实际上都比我们严重。比如2010年时巴西的增长速度是7.5,2015年是-3.8,去年是-3.4,它也是连续七年下滑,下滑的幅度都比我们深。俄罗斯2010年增长速度4.5,2015年-3.7,去年-0.6,同样下滑,下滑幅度比我们深。印度2010年增长速度10.3,去年的增长速度是6.5,也是一样下滑的。
它们没有我们这些体制机制问题,比如我们经常讲的体制问题,国有企业比重太高,国有企业效率低,它们没有国有企业的问题,因为像俄罗斯国有企业早都私有化了,巴西、印度是以私有企业为主的。我们常讲我们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是因为投资太多、消费太少,它们国家都没有投资太多的问题,同样是这个问题。
另外我常讲,不仅是这些金砖国家,我们也可以看东亚这些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同样的情形,比如说新加坡,2010年的增长速度15.2,去年是2,韩国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5,去年2.6,下滑幅度比我们高。我记得台湾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8,比大陆还高,去年增长速度没达到2。这些都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也就是说,它是高收高表现,也就是我们存在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它们基本没有,怎么样会这样子?其实道理就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还没走出来,发达国家长期的平均增长速度像美国应该是3.5,去年只有1.6,欧盟国家也一样,去年差不多1.6,日本去年是1%的增长,都没有达到3.5。
在这样一个国际周期之下,发达国家发展不好,出口一定减少,2008年每个国家、每个经济体都采取了一些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进行一些投资,这些反周期的政策基本上五六年的时间都健康(音)了,但是国际经济还没有恢复,所以大家投资的积极性低,这是我们现在经济下滑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这种情况下怎么恢复我们的信心?这是相对而言的,我们跟其他发达国家比,我们的投资机会多不多。比如说发达国家现在能找到很多投资机会,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在经济下滑的时候,跟我们一样面临所谓产能过剩,但是它的产能过剩是在全世界最先进的产业上产能过剩。这种状况下它要投资,我们现在讲有所谓的3D打印、电动汽车,你只有一两种产品的创新,那方面的投资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
我们现在也讲产能过剩,但是我们的产能过剩都在中低端,我们在向高端升级,而且向高端升级的空间非常大。比如去年我们单单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1.2万亿美元,国内自己不能生产,那我们不能升级。这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现在进口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的产品,它想把这些产业拿到美国去,美国的工资那么高,它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根本没竞争力。但是我们的产业升级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多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要分清形势,我们经济下滑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产业投资升级的空间要什么地方,这样搞清楚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的。因为确实像我们现在讲的维持每年6.5,争取达到6.5以上是完全有条件的,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现在的经济占全世界经济的15%,6.5%以上增长,每年对世界的贡献就是一个百分点,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是3%,我们每年对世界市场扩张30%在中国,这是多好的机会!所以我们的工业部门、企业家是可以有信心的,如果把问题分析清楚,跟自己在这种国际整个的疲软周期当中,我们的机会还是最好的,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工业部门可以有信心。
媒体: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大家有一个解读说今年的经济要脱虚向实,是什么原因导致脱虚向实,是因为政府不够有为还是市场不够有效?我想听听您对这个的看法。
林毅夫:这里面有这样的情形,确实过去这一两年房地产的问题、股票市场的问题,价格上涨太快,股票市场价格上涨不可持续又跌回来,现在房地产也在高位,这个确实引起大家的关注。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我们经济在一个疲软的周期,基本上你用的政策无非就是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是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知道资金的导向会到哪边去,我们希望资金的导向是向实体经济,但是大家在不清楚整个经济下滑的原因是什么、未来的发展展望是什么的时候,对实体经济投资的积极性也不高,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进入到来得快、有一点投机性的地方去,那就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我们如果要让经济发展在这种国际下滑周期时发展得比较好,一方面应该更多地依赖财政政策,用财政政策的扩张来支持一些属于短板领域的投资。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短板领域里面基础设施还有短板,尤其是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环境有短板,城镇化有短板。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合适的投资增长。
在这种情况之下,民间对实体经济里面产业升级投资的积极性会比较高,当然,也必须把银行跟金融机构的资金更多地引导到实体经济的投资上去。如果能这样做的话,我们既可以维持经济比较稳定地发展,也可以避免大家所担心的金融机构以及一些虚拟经济过度的发展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意想不到的风险。
媒体:林老师好,我们在博鳌刚开始的时候收到一个关于亚洲竞争力报告的内容,其中台湾在2017年的综合竞争力报告可能排在第四,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两岸关系目前比较复杂,台当局实施的是新南向的经济政策,不管是两岸三地都有一些学界和业界的声音,认为可能这个政策很不好推行。您觉得这个新南向政策真的有那么多的阻碍吗?您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林毅夫:第一次南向政策给台湾带来的后果已经非常明显,比如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比韩国高,当时台湾的人均GDP比韩国高大约30%,现在韩国高我们台湾30%,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干扰经济。实际上台湾跟大陆的经济是高度互补的,因为台湾的经济要继续发展,生产力水平要提高,它的条件就是必须把它失掉比较有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可以创造“第二春”的地方来,大陆的其实是最好的地方。
如果它能够把台湾的失掉的比较利益(这边叫“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大陆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好处,它就把原来投资在产业这些死的资本变成到大陆投资的活的资本,可以利用大陆的有利条件做更大的发展。这里面如果能这样做的企业都做得相当成功,比如我们知道台湾的裕元(在大陆叫“宝成”),它在台湾的时候只不过2千多个人的中等工厂,利用大陆丰富的劳动力发展到50万个人的企业,如果不到大陆它就没有这个机会。
当时因为很多政治上的原因,该转移到大陆的产业不能转移,比如当时的台积电,当台积电12英寸晶圆片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台积电应该把8英寸转移到大陆来,然后腾出空间去发展12英寸。但是当时你不让8英寸的来,所以导致12英寸的升级比较慢,这样就导致整个台湾的经济生产的速度放慢。
如果你能转移过来,好处就是你腾出空间、腾出资源,而且大陆这边发展以后,也给台湾产业升级的产品创造巨大的需求,台湾没有抓住这个机会,韩国抓住这个机会了。基本上它跟大陆建交以后就快速利用韩国跟台湾的经济基本处于互补,把它失掉优势的产业转到大陆发展,它进行产业升级,又利用大陆的市场让它有更大的盈利,有盈利以后进行产业升级。
90年代的南向政策已经证明从政治来干预经济,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是极端不利的。作为台湾人我一再强调,其他方面可能输,但是有一样绝对不能输——经济上不能输,经济上一输全盘皆输。
所以如果台湾的当政者真的考虑我们台湾人的利益。我1979年刚到大陆来,大陆这么穷,中国人到哪个地方去人家都瞧不起。为什么今天中国在国际上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是经济发展起来的。八九十年代,我记得我的老爸爸来看我的时候,那是1989年,我爸爸是一个农民,他信心满满的,他到大陆来以后到处指点江山,这个应该怎么做、那个应该怎么做,我们台湾这么做可以做得好,大陆这么做就可以做得好,一个农民都有这样的信心。到了90年代末我姐姐来看我,看我以后两相对比,就开始想说大陆有什么工作,我们来这边做点小本生意,比在台湾好。
所以我想,真的是,如果台湾的政治领导关心台湾人民的利益,一定要从大处着眼。如果经济输了,台湾输了。当然,如果大陆经济输了,大陆也是什么东西都输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绝对不能够放弃的原则。
所以新南向政策我自己是怀疑的,我认为从过去跟着南向政策去的企业大部分断羽而归,如果新南向政策真要推行,大部分的企业不会去,如果真的去,也是断羽而归。我觉得台湾应该在经济上抓住大陆现在每年的经济增长还是世界经济增长30%以上的机会,然后让台湾的经济更好地发展,这样台湾才有前途。
Comments are closed.